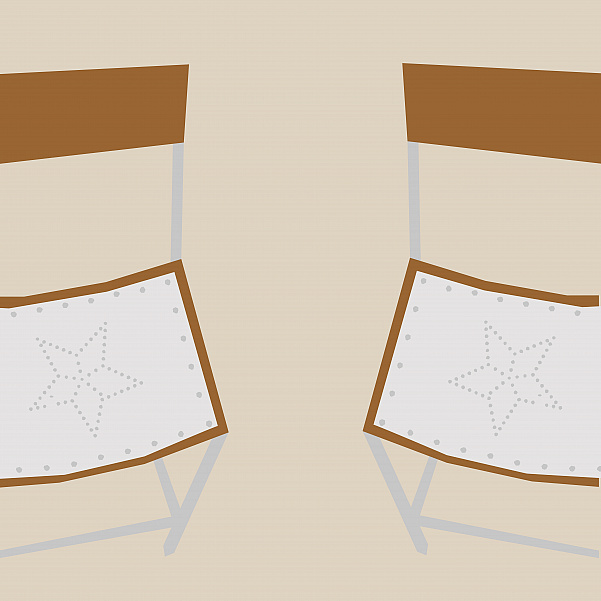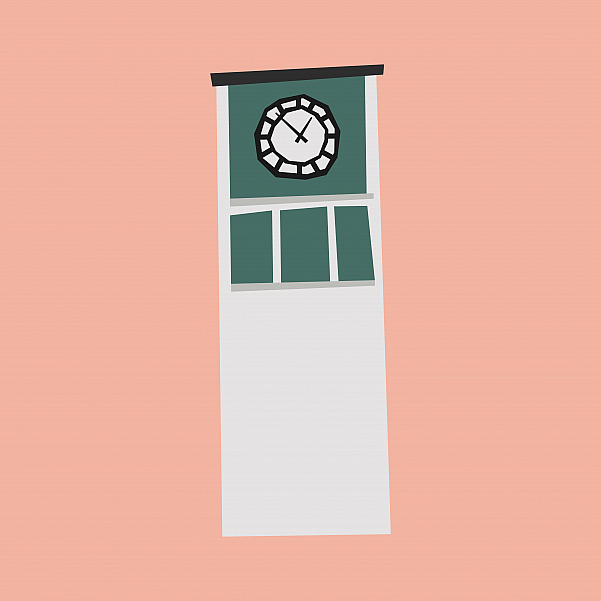文:賴崇欣
一、
阿偉在灣仔碼頭準備開工,在員工休息室換上深藍白邊領口的的水手服。新批次的水手服較七、八年前舊的、粗糙的夏季短袖制服沒那麼不透氣。想起二十幾年前,第一天在天星碼頭上班。他本來在啟德機場擔任地勤,在禁區輸送行李。1998年機場要搬,飛機在頭頂掠過上空的情景不再,他在報紙上見到天星小輪請水手,就去應徵,手拿由機場發的離職信,簡單見過主管和經理,就被取錄為碼頭水手。第二天還未驗身,就已開工。那天,他先從旁觀察師傅學勾纜、上纜。在舊中環碼頭上班。二十幾年轉眼間過了,這二十幾年間,碼頭拆了兩轉又起了兩轉,尖沙咀往返灣仔的船程短了兩分鐘。他按潮漲潮退調教升降台、勾纜、上纜、開閘、閂閘、解纜也成了手板眼見工夫。
二、
五月期間的放工時間,阿儀在灣仔碼頭不是登上「午星」就是「日星」。六月,則就登上了「熒星」與「曉星」。小輪也有它們的更表,每隔一個月,小輪就會對調航線(阿偉亦不解為何如此運作)。一星期總有幾天。放工後她會乘小輪去到尖沙咀,再轉巴士回家。坐在星星木椅看晚霞的短短的七分鐘,一切勞累都溶到一江綠水之中。天星小輛的白代表天空、綠代表海洋,所以它是行走於天與海之間的使者。
她覺得船與碼頭是一對戀人,年年月月,不斷不斷地親吻。哦,但若如此,那船實在是花心的一方。船是雙頭龍,船不用調頭,就可以駛回對岸。兩頭都到岸,兩頭都到岸,阿儀希望她的人生頭頭也到岸。
三、
工作於阿偉來說,不外乎是適應。他適應了輪更的工作——有時返早更,六、七點開工,有時返夜更,一點至三點之間開工。他在三個碼頭輪流返工,每四日就會調到另一個碼頭工作,每返二十日或者十六日就放四日假。放假於他是「放監」。放監,他會去牛池灣飲茶食點心,再到西貢找機場相識的老朋友。他喜歡返早更,可早點回家,多點私人時間。天口熱,他開了房間的冷氣,小睡片刻。
他也適應了日曬雨淋。那天眼看對岸放晴,他卻被傾盤大雨淋照頭淋了一分鐘,下雨就穿雨衣、太陽曬就戴上有天星標誌的帽。冬天穿長袖制服外,他會加件背心羽絨,外穿公司的風褸。除了八號風球,水手們也要謹守崗位。黑雨的頭一兩個小時,小輪仍會在一片白茫茫中航行。
四、
阿儀走過鷹君中心的天橋,穿過粉紅假花走廊,就可以在電子鐘上看到下一班船的開出時間。18:58,現在18:57,要跑了。又有時船是會遲到,遲到會令阿儀趕不上巴士的特快班次,在候船室等候時她難免焦急起來(儘管她深知焦急不會令船行得更快)。登了船,她坐在近吊板的位置,好在吊板啪一聲落下時就可衝落船。
下船之際,她隱約聽木箱鼓與電結他聲,下樓梯見到三個年輕人在近旗杆的有蓋空地演唱,約十人圍觀細聽。「活得精彩結尾切勿流眼淚……」兩個男聲和唱悅耳,但她不得不快步趕巴士。後來,她重遇他們,那次可以駐足細聽。
五、
他不喜歡船客在響了鐘以後還慢慢行,他原地跑起來,叫人加快腳步。有時,船客還會罵他不等他才開船,他們不知道,在繁忙時段,有三班船行在同一條航線,每七分鐘就有一班船靠岸。上一班船沒有開出,另一班船只可以在海中心等候。為了抓緊時間,他不得不冷血地閂閘,也因而不得不受幾句的咒罵。今天一個船客以「我腳痛唔跑得」為由叫阿偉等埋。阿偉心想:「諸多藉口!」。但為免被投訴,他等了他,但下一班要遲兩分鐘,再下一班也會遲兩分鐘……..
六、
關於拆碼頭,他只是想一定有人反對,有人支持。舊以前的灣仔碼頭站台比較窄,在其上工作並不如現在的安全。尖沙咀碼頭的洗手間在有自由行開放時期,廁所因使用量高不時會溢出屎水。及後,化糞池加大了,問題才得以改善。他明白有些人懷舊,他也沒有忘記自己在舊中環、灣仔碼頭釣魚時的興致,但他似乎也沒有被過去抓住的因由。現在,他會滑滑手機,同事們會捉小精靈,踱步幾回,船又埋岸了。
七、
2006年時她不過十歲,對於拆中環的鐘樓沒有太多的記憶。她後來在網上看到抗議中環碼頭遷拆的片段──一大批的市民在11月11日夜晚送別中環舊碼頭,在對出的空地點起一列白蠟燭,欄杆上掛滿藍絲帶和「不要拆我們的集體回憶」等標語。有人扮成為鐘樓,遊走於兩岸。11月12日的午夜12時,鐘樓響起最後的鐘聲,有人吹哨,有人鼓掌、有人靜默。小輪響號,大家在鐘樓前影相留念。
海可以填、鐘樓可以拆。阿儀覺得沒有甚麼是不變的。
不,潮漲潮退不會變,日升日落也不會停,海風不止拂拭,海浪聲不絕。
她頓覺心安。